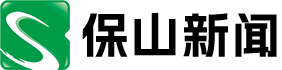《谈“十观”—杨善洲精神蕴含的思想方法论》之生态观

编者按:
早在1924年,瞿秋白就在《社会科学概论》中提出过“思想方法(‘时代逻辑’)”的概念。1936年,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艾思奇专门写成《思想方法论》一书,毛泽东研读后作了批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建立研究组(学习组),其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提出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当时,毛泽东还委任艾思奇负责总编,集中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供整风学习使用。这本书被习仲勋称为当年读过的书中“最好的哲学书。”思想方法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思想方法,是指“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观察、研究事物和现象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是关于主观反映客观,即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基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立场观点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根本性。”也就是说,思想方法是如何看问题、怎样想问题的思维之维,是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根本之点。
“欲事立须是心立。”艾思奇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的可贵处,就在于它能够把事物的真理,反映到我们头脑里,使我们对于事物有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在改变事物的行动中才有正确的方法。”思想乃行动之先导,一个人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想问题,就会付诸什么样的行动去解决问题,正像德国诗人海涅所说的:“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如果用杨善洲的话讲,就是:“水库河堤冲垮了,思想不能垮;房屋财产受灾,思想不能受灾;草谷发霉,思想不能发霉。”思想方法不对头,看问题看得不准确,想问题想得不正确,工作方法也就不对路,干起事情来就有可能走偏走错,甚至南辕北辙。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常常出现“我一直在思考”“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常在想”“我经常想”等话语。他多次指出,党的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要心怀‘国之大者’,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等等。杨善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和长远的向度,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判断形势、辨别是非、观察事物、思考工作,一生都初心不改、使命不忘、信仰不变、立场不移、方向不偏,从而形成了杨善洲精神中最具灵魂性本原性的部分——正确的思想方法论。而且,杨善洲精神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不是一块黄土,而是一颗有着无数个面的钻石,“一块黄土,风一吹雨一打就碎;而一颗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亮。”我从杨善洲一生的实践中提炼出的思想方法“十观”,只不过是这颗钻石的其中一个面,或几个面而已。


第九,生态观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既是“人文”,也是“天文”,其中蕴含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层观念。《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古语,表达了先人们对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深刻认知。孔子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些观念,强调了不违背自然规律进行耕种就能获得丰收的深刻道理。《吕氏春秋》提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白居易告诫人们:“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这些思想,指出了如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违背规律过度索取,就会遭受自然界“报复”的深刻哲理。当历史的指针走到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考察后,面对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的疑问,他撰写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首次提出著名的“两山”理论。他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之后不久,就鲜明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大理洱海时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上世纪70年代,如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由于长期的乱砍滥伐,保山的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的52%下降到28%,造成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袭来。特别是1979年,保山遭遇70年未曾有过的大旱,8个月里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昌宁县新街小公社,因小河上游山林被砍光,1978年遭受洪灾,泥沙掩没了大片稻田。通过3年的努力恢复,刚见成效,谁料1981年又是一场暴雨,山洪再次暴发,小河冲下的泥沙淹没了1000多亩良田。杨善洲当时已是地委书记,他从调查中深刻认识到植树造林、生态环境的重要,并且总结出一些顺口溜:“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山上没有树,水土保不住”“山上毁林开荒,山下一定遭殃”“山区要致富,多栽茶和树。”杨善洲从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的角度指出:“过去我们缺乏长远建设的思想,忽视了发展林业生产,现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过去30年,森林覆盖率从52%下降到28%,照此下去,20年后,现有森林就砍完了,不但下一代没有木材可用,就是我们这一代也没有柴火可烧。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更突出的是林业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山穷水尽’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抗的自然规律。”1985年,杨善洲深入高黎贡山沿线村庄调研,他到瑞滇区联族村时指出:“不能依靠砍树来做一条门路,要找其他门路!应该是‘靠山养山,种树致富’。更重要的还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盛复健曾回忆,1986年老麦乡要完成1000亩种茶指标,荒山不够,只能毁林种茶。杨善洲知道后,跟县领导说:“要保护好青山,不能毁林种茶,老麦乡完不成就算了,保护生态最重要。”他极有见地的指出:“在发展茶叶的同时,还要保护好现有的树林,荒山空地也要植树造林,不能坐吃山空。”盛复健深有感触的说:“在那个时候,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很多人盲目抓经济发展,做了许多破坏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事,但杨善洲书记就能想到要保护生态、绿化荒山,宁愿完成不了指标,也不能破坏生态。……杨善洲书记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在当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就能提出保护生态这一说法,跟我们今天国家所提倡的生态观念不谋而合。”1987年,杨善洲就林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总结出营林、管理的8种形式,并将其分为4类,深入分析利弊,形成了《关于继续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地委办的《情况通报》印发。他指出:“森林是‘绿色银行’,不论中幼林还是成材林,都具有现实的经济价值。”退休之后,杨善洲登上了“半年雨水半年霜”的大亮山,开始长达22年造林生涯,“绿了荒山,白了头发”,亲手缔造出了一座他口中的“绿色银行”。当时,曾有人劝杨善洲不要上山种树,在机关整理档案每个月还可以拿三四百块钱。杨善洲回答道:“上山造林是绿化荒山,种树是保护生态,我是要树不要钱。”初上大亮山建林场时,面对荒山风沙,他说:“栽下一棵树,山就会绿一小块,栽下几棵树,山就会绿一片,我就不相信这山绿不起来。等到山绿了,风沙就会越来越小了。”杨善洲用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践行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生态观,并且以大公之举,把5.6亿亩绿水青山奉还国与民,“不与桃李争春风,撑住乾坤几霜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杨善洲先后获得“全国绿化奖章”“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华环境奖”“‘2010年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特别奖”等荣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一重要论述,分别从民心、民生两个维度审视生态环境,特别具有时代高度。从民心的维度看,生态环境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民生的维度看,生态环境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事关民生福祉。作为党的干部,就应该像杨善洲那样,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持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保山良好形象的着力点,让永昌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更蓝、空气更优、环境更美,绘就“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和“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的美丽画卷,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025年度杨善洲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杨善洲精神蕴含的思想方法论”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共保山市委党校课题组
一审:杨娜
二审:杨冬燕 杨娜
三审:王灿
滇ICP备 11003008 号
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主管 保山网版权所有 未经保山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