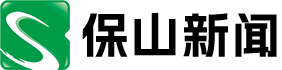红木树古道百年风云
从惠人桥上高黎贡山红木树,眼前豁然开朗,站在海拔1620米的台地上,潞江坝尽收眼底;向后,山峰耸立,继续攀爬至象脖子、大风口,则可通太平铺下龙川江。所以,红木树既是一个行人心理上躲避瘴气的理想地,又是一个身体可以休息的驿站,更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军事要地。1944年5月,著名的红木树之战缴获的情报,揭开了滇西反攻战术改变的重大秘密。
·1·
红木树,高黎贡山古村落,最初因村落周边长有多棵红木树而得名。红木树的学名叫木荷,二十多米高的大树直入云天,仿佛直达天界。如果是夏天,枝干开满白色花朵,花瓣形似荷花,朵朵相簇,黄色花蕊又散发奇香,过去古道上行走的人常常在树下乘凉。

红木树古道。
红木树古道是一条清代以后兴起的翻越高黎贡的通道。起因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就江心大石,复以巨石垒之”的惠人桥正式落成,无数马帮商队过惠人桥上红木树,再经象脖子、风口梁子、黄竹园接元明古驿道太平铺下龙川江到腾越。
直线距离上,红木树古道要比元明时期的蒲满哨—大蛇腰—太平铺古道近许多。徐霞客1639年农历四月十二过道街渡(现东风桥下游1.5公里处,东岸为道街村农田,西岸为热作所实验地),乘船渡怒江,然后登高黎贡山,经磨盘石(石梯寨)、蒲满哨、城门洞(翻山丫口)到太平铺,再到竹笆铺、腾越州城。而美国旅行家盖洛1903年3月6日过惠人桥经红木树到太平铺,比徐霞客少用了大半天时间。

曾经的红木树古驿站。
红木树海拔1620米,它作为古驿站存在时,凉爽的气候打消了过往客商对瘴疠的恐惧,他们得以安然入睡。盖洛用400字的篇幅,为我们重现120多年前的红木树现场提供了文字依据。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里,盖洛写道:
当我们往山上走了许久以后,回头还能看到那座铁索桥。从红木树(Homoshu)看下来的景色是最美的。此处的高度是海拔5560英尺。而怒江的高度则是海拔2430英尺。下面的平原,稻田纵横,圆锥形的山峦此起彼伏,静静流淌的怒江,以及两岸远处的山峦溪谷,勾画出了一派迷人的自然景观,真能让那些爱好自然的人们流连忘返。
红木树是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街道都是用石板铺成,房屋则是用泥砖垒成的。竹管把纯净的溪水送到各家各户,供人畜饮用。这里是著名的天福头绵羊的故乡。有一位居民,所谓山里的预言家告诉我,过去汉人是不敢在这个平原上停留的,但现在他们只是在雨季才离开这里。那时,厘金局的收税官们会上山去休养。在雨季,人们在早晨会看到山谷里红、蓝、黄这3种颜色的雾气。如果外来人吸进这些雾气,那么他们就会丧命。在一场夏雨之后,致命的雾气就会慢慢地在这个美丽的山谷弥漫,将它笼罩在死亡之中。雨水浇在这儿的黄土之上时,黄色的妖怪就会吐出黄色的雾气来。
盖洛还在后面的文字里叙述,随行的一个姓李的脚夫在上太平铺的途中病倒了,躺在路边痛苦地蠕动。盖洛给他吃了药,其他脚夫则用土办法给他“揪痧”:把他的臂膀露出来,用水洗他的肘部内侧,抓捏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关节处,还有他的颈部。这都是对抗刺激疗法。然后有人给他嘴里塞了一个姜块。之后他坐在盖洛的滑杆里,不一会儿就好了许多。第二天,几个喝了生水的脚夫也病倒了,还发起了高烧,都在诅咒那该死的山谷及其雾气。盖洛同样给他们服了药就好了。他分析这里的瘟疫产生的原因,首先这个地区本身就不太卫生,那些苦力和其他人又心存恐惧和不安,从而造成身心疲惫,再加上喝了那些没有烧开的生水,虚弱的身体就会支撑不住而病倒。于是他们就以为是误吞了那些雾气。
盖洛是带着一个现代的外来人来分析当地的疫病的,而且他只是路过一次,远不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对瘴气的恐惧,连徐霞客当年都只敢夜宿东岸半山腰。这一点可以在盖洛文字里描述的惠人桥东岸的“捕妖台”窥见一斑。盖洛黄昏前到达惠人桥东岸,及时拍摄到了台阶旁的捕妖台,然后过江到了桥西岸,住进了厘金局。坐在厘金局的门廊上,“看到桥对面的那个捕妖台里传来了亮光,因为有人点亮了那儿的一个灯盏。”他两次提到捕妖台,不免让人产生好奇,捕妖台是干什么的呢?我也是第一次在众多的中外旅行家的笔记里看到这个词,估计当时盖洛也很好奇。他问遍桥头村庄里的人,人家告诉他江里有个制造瘴气的妖怪,靠吃掉进江里的人和骡子为生,如果没有人和骡子掉进江,它就会爬出来吞噬人和骡子,所以,村里人就在东岸桥头它容易出没的地方设了个捕妖台。哈,至于百余年前有没有捕到妖,就留给盖洛去想了。关于瘴气的产生,后来的科学解释已有很多。
·2·
基本是沿着盖洛的路线,我们从莫卡村到达山脚的禾木村。禾木村是红木树的新寨子,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山上搬迁下来的,且更改了名字。盘山而上,路只是森林消防通道,陡峭狭窄,间或有古道石板路,步行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红木树。
不到红木树,不会发现这个位置的精妙。我倚在杨龙周家的楂子树下,来时道路的各种弯曲已经藏匿在树林里,越过各种树木的头顶,视野的正前方依次是惠人桥、东风桥、怒江新大桥、曼海桥及整个潞江坝,比较下来,红木树是从潞江坝翻越高黎贡南线到龙川江的最便捷的通道,难怪1944年日军要死死守住不放。
在盖洛描述的红木树村的街子上,一条残存的石板路上闲逛着杨龙周家的猪鸡狗羊,几间曾经的马店如今被当作杂物间。我们一眼就相中了楂子树下的小方桌,围坐在树下喝茶。这棵楂子树生命力真强劲,主人家用竹篾笆编的厨房就像挂在它身上,火塘烟雾缭绕,烟雾不断从篾缝里钻出来,嫩绿的楂子时不时在烟雾中探出头来。杨龙周的妻子杨丽苹泡好茶就去端来一箩新收的核桃,再掏了一碗蜂蜜,蜂蜜蘸核桃,这是待客的最高礼节了。杨丽苹说楂子树三月份开花的时候最好看,白花花的一树,坐在树下就舍不得站起来。我想象着春天楂子一树繁花的情景,还真有点羡慕她的生活。

红木树学名叫木荷,二十多米高的大树直入云天。黄湘元摄
吃够了蜂蜜蘸核桃,我站起来走到紧挨着楂子树的柿子树下,发现这间竹篾笆房的另一端,是搭在一堵废弃的土墙上,原来是杨龙周爷爷那辈建盖的土基茅草房,杨龙周就出生在那间房子里。30多户村民70多年前搬迁下坝后,房子慢慢就倒了。几代人的记忆和梦想就存在于那些残缺的土墙和依然年年岁岁奉献着果实的百年核桃树上。

在红木树居住的杨龙周、杨丽苹夫妇。
今天一起上山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因为担心雨季过后路有塌陷,老朋友左仁杰特意约上了村里的苏德杰、张从杰、陈在刚、郭家华4人,他们骑着电三轮、带着锄头为我们护路。他们虽然住在山下禾木村禾木小组,但咖啡地都在山上,沿途六七百亩咖啡郁郁葱葱,叶和果都油光水滑。说起咖啡,他们都很兴奋,今年咖啡价格好,陈在刚的40余亩咖啡毛收入达到40多万元,杨龙周夫妻俩收入10多万元,种植面积最少的也有4、5万元。

这几朵帽子大的黄鸡枞是红木树密林常有的惊喜。
禾木村副主任苏德杰出生在红木树上面的羊场,1982年他8岁时才下山,也是最后一个下坝的人。他对红木树、魏家寨、羊场、象脖子一线了如指掌,前不久还从象脖子走到大松坡、风口梁子、太平铺(烽火台),去看沿途的古道和滇西抗战时期的战壕、掩体、弹坑等遗迹是否被雨水冲坏。左仁杰也是红木树人,他出去读书后就一直在保山工作,也是一个资深的徒步达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红木树古道就是跟他来的。他们俩有一个想法,大风口以西的古道属于腾冲芒棒镇辖区,腾冲已将古道与抗战遗迹资源做成“古道花海”徒步项目,非常受欢迎,他们也想探索红木树古道接太平铺的文旅方式,所以对这一区域的自然和文化背景非常感兴趣。接下来他们带我和同事沿古道方向查看红木树周边的抗战遗迹——1945年5月11日开始的滇西反攻战之高黎贡红木树之战,是高黎贡南线最有故事、最具反转效果的战斗。
·3·
1944年5月11日夜晚,中国远征军在卫立煌将军指挥下,在300公里的范围内正面横渡怒江天险,分左、右两翼,向侵占腾冲、龙陵的日寇发起反攻。
反攻计划的要点,是担任右翼攻击的二十集团军十万大军,在霍揆彰将军的指挥下,北从西浪渡口、南至双虹桥渡过怒江后,对固守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冷水沟之敌发动勇猛攻击,而后横扫腾北,收复腾冲;担任左翼攻击的十一集团军十万大军在宋希濂将军指挥下,沿惠人桥、攀枝花渡、三江口一线,对固守松山之敌发起攻击,然后由北向南往滇缅公路方向包围夹击日军,占领滇西重镇龙陵,之后打通中印公路,策动驻印军反攻密支那,实现中缅印战场的胜利。
但是,渡江很顺利,反攻高黎贡的伤亡却远超预期。以71军新编39师师长洪行指挥的115团、116团为例。洪行的任务是打下高黎贡山上的红木树、龙川江两岸橄榄寨的日军阵地后,伺机奇袭腾冲城,端日寇的老窝。115团作为加强团,任务是从惠人桥一带渡江牵制敌人。在战略位置上,海拔1620米的红木树位于高黎贡东坡的制高点上,也处于二十集团军和十一集团军的结合部上,能俯瞰整个潞江坝,如果拿下红木树,既可以切断芒市方向的援军,又可以切断腾冲日军溃逃的后路。但驻防红木树的日军是驻守松山的113联队第一大队一部,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115团团长派先头连于5月10日连夜渡江。连长朱开诚在夜幕掩护下,率100余人经盘蛇谷急进到惠人桥东岸,原架在东西两岸的铁索桥早已破坏,先头连乘船率先渡过怒江,在新寨村潜伏下来。此次仰攻高黎贡,北线为南、北斋公房、冷水沟一线,南线为惠人桥上红木树一线。先头连在新寨村潜伏一天,等待北线攻击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冷水沟之敌的消息。5月12日凌晨5点20分,先头连沿陡峭的山路绕向红木树,悄然到达红木树日寇阵地,但进村时未遇到任何抵抗。自从日军入侵以来,这里的几十户山民早已逃散,躲进了深山老林。因为此时高黎贡的反攻还在南、北斋公房进行,红木树相对平静,当先头连突然而至,日军守敌200余人紧急应战,抵挡不住而后撤。20日凌晨,日军组织大队人马疯狂反扑,先头连后援跟不上,只能撤出。当日夜,先头连补充人员后,再度对红木树发起攻击,但敌人已做足准备,铁丝网把他们自己的阵地重重围住,先头连费尽力气潜入,却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夹击下无还手之力,连长朱开诚阵亡,前来增援的115团三个营全部阵亡。
其他位置,如大塘子、南北斋公房垭口等等,均遇到巨大伤亡。在渡江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中国远征军伤亡近万人。
庆幸的是,115团先头连红木树撤出时,缴获了一套日军地图,21日这套地图拿到11集团军司令部后,宋希濂大拍桌子,这个地图跟他在司令部看到的地图一模一样!日军根据我们的进攻首先打高黎贡山的部署,加强了兵力,宋就打电话报告卫立煌,卫立煌赶到11集团军前线,这个情报让卫立煌大吃一惊,瞬间明白攻击受困的原因,同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部署进攻高黎贡山,很可能打不下来,整个滇西的反攻就会失败。而驻印缅军5月份已经开始进攻密支那了,如果滇西战场没有远征军的策动,那整个中缅印战区准备打通这条中印公路的计划就无限期推迟。如果远征军20万大军不能战胜3万日军,那失败的影响会很快波及缅北,印度英帕尔及整个亚太战场,日本人很可能乘胜进击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太战场就会因一个局部的怒江战役发生难以预料的失败。
他立即召集宋希濂和霍揆彰紧急商议对策,秘密调整战略部署。从红木树缴获的日军地图上,远征军高层发现松山日本军队空虚,他们的兵力大都调往高黎贡山了。于是远征军高层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作战计划,将计就计,右翼二十集团军持续做出进攻姿态,迷惑日军,原先作佯攻的左翼十一集团军的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南行进,提前总攻松山,控制滇缅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卫立煌亲自赴重庆报告后,长官部于22日、23日两次下达作战命令:1、远征军即全部渡江攻击,重点指向龙陵。2、第20集团军照原计划攻击,目标是腾冲。3、第11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限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1944年6月1日,第一批中国远征军出现在松山阵地,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红木树之战留下的掩体。
至于反攻计划当时为什么会泄密?抗战研究学者戈叔亚后来在日本的《公开战史》上看到这个事件的内幕,原来是反攻前中国远征军的一架飞机欲飞到印度北部与中国驻印军联系时,飞机出事故掉到腾冲境内,一个高级参谋带着很多文件来不及烧毁,被日军抓获,这份文件就中国远征军是反攻滇西的整个计划。日军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早在5月5日就把各团队长召集到芒市,宣布已获知中国远征军的主攻方向,将防御和反击重兵北移高黎贡山,即把56师团中的近1万人转移到高黎贡山、龙川江河谷和腾冲城区,派水上源藏少将指挥立即行动,对突击的远征军实施各个击破。
多年进行抗战研究的学者李枝彩查了当时的远征军战报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5月29日,负责左翼牵制任务的第11集团军奉命全线反攻,新39师116团于当日从惠人桥渡江,沿丝绸古道一路激战,于6月10日推进至潞江坝西缘的红木山下。6月11日,该团兵分三路向红木树守敌发起猛攻,在惠人桥东岸我71军山炮连的猛烈炮火支援下,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于12日上午将红木树守敌200余人全部击溃,打开了该线反攻大军跨越高黎贡山的第一道大门。”
过后不久《陆军新编39师怒江两岸高黎贡山之役战斗详报》这样评价红木树之战:“搜索连少校储备参谋兼连长朱开诚,红木树之役,能出奇制胜,忠勇善战,智略超人,首克要点,开远征军胜利之先声。”
刁丽俊/文 范南丹/图
一审:李秋
二审:杨冬燕 杨娜
三审:王灿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 53120250003
滇ICP备 11003008 号
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主管 保山网版权所有 未经保山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